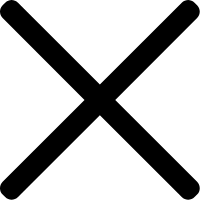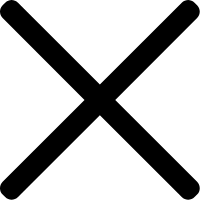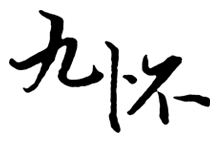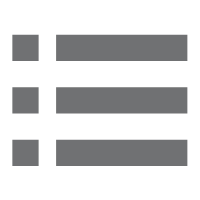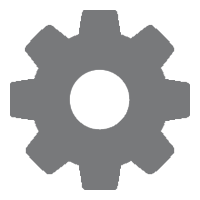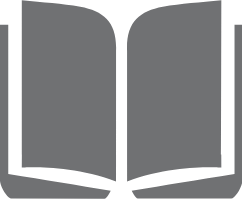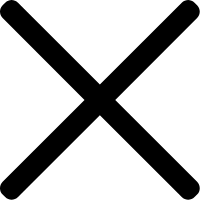儿子回家,老子社死。
时隔两个月,齐麟终于回家了,一进家门就目睹了一幕好戏。
客厅没人,厨房那头飘来饭香。
锅里炖着鸡汤,李维宁在一旁切菜,齐海从后面搂着他,嘴上卖着骚不说,还动手动脚的。
齐麟本想去冰箱开罐可乐的,没想到就看到了这刺激晃眼的一幕。
眼看着齐海的手就要摸进了围裙,齐麟咳了一声说:“我回来了。”
这一声着实吓坏了齐海,人瞬间就跟炸了毛似的一步跳开,脸上是大写的尴尬。
“好好的怎么回来了?”
“……”
齐麟无语,心道:不是你打电话求我回来的吗?
李维宁也有些不自在,但很快就恢复如常,笑着停下了他手里的活儿,“回来的正好,马上就开饭。”
“哼,”齐海脸色泛红,嘴里嘟囔着,“可真会挑时候。”
“抱歉,影响你们二人世界了?”齐麟似问非问转身就出去了。
这一走搞的齐海心里挺不是滋味的,因为齐海分明瞥见了儿子眼里的落寞和失望。
齐海看向李维宁,不知如何是好。
他和李维宁那一摊事,不是一两句能说得清的,还有他们的关系,更是从来没跟齐麟提过。
父子俩一直以来,一个聪明,一个装傻,都默契的选择了沉默,没有捅破那一层窗户子。
齐海不是不想说,是他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,他不知道要如何面对齐麟。
儿子跟他出柜的时候,他怒不可竭将人打了一顿,其实自己早就跟个男人在一起了。
他瞧不上儿子找了个老男人,父子关系一度岌岌可危,而儿子却从始至终都没反对过他和李维宁。
齐海不是不知道,自己是有点双标不讲理的,可他习惯了家里家外掌控一切,他也强势惯了。
齐麟那一抹受伤的神情,却让他心里十分不是滋味。
“去吧,和他谈谈。”李维宁倒是很平静,说着就继续干活了。
客厅里,齐麟心里数着数,等着人主动来找他谈,他还反复确认了一遍,自己刚才并没有露出破绽,表现已经足够“受伤”了。
接着身后传来一声轻咳,是齐海。
齐海手里拿着罐可乐,在齐麟对面坐了下来,然后将可乐往齐麟那推了推。
“天冷,就别喝冰的了。”齐海不带表情的说。
齐麟情绪不高的“嗯”了声,齐海见齐麟那张丧脸,心又软了。
“我跟你叔儿、我们,你应该早就知道了吧。”齐海强作镇定的说。
说完,心里的千斤顶也跟着落地了,然而还没畅快两秒,就听齐麟反问道:“知道什么?”
“……”齐海脸色霎时红了一片。
小兔崽子,这是非得他一字不差的说了才满意?齐海臊的直上头,“爱知道不知道,老子犯得着要跟你汇报。”
毫无意外,齐麟死气沉沉的顶了嘴。
“您的事我从来不管,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样,我习惯了,您不想说,我就当没这回事。”
“……”齐海气汹汹的却插不上嘴。
“我这次回来,主要是看叔儿的,我打算给他介绍个人,他这个数岁,不能总这么不清不楚的跟您混,他得安个家,您说呢?”
齐海一口气没上上来,瞳孔里着了火一般,脱口而出:“你特么敢!”
“我是您生的,”齐麟毫无畏惧之意,“我有什么不敢的。”
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,父子又杠上了。
李维宁此时就在厨房门口,他一边看着俩人剑拔弩张,一边瞧着锅里的鸡汤咕嘟嘟,然后悠闲、淡定的点了根烟。
齐海嘴都快气歪了,“你他娘的。”
“我没娘!”齐麟咬牙道。
这是杀手锏,这是耍无赖,这是对准齐海的软肋戳刀子。
空气陡然凝滞,凉意刺骨,气压极低。
齐海心颤着,呼吸也颤着,他混乱的手足无措。齐麟看向他,眼里也满是无助。
齐麟叫了声“爸”,话音像泄了气的皮球,他问齐海:“跟我说个实话就这么难吗?”
齐海怔愣,心脏砰砰的,这么多年,齐麟除了搬出宿舍自己住,就没在跟他提过任何要求。
如今提了要求,却也只是要他一句话而已。
齐海沉沉叹了口气,一抹苦笑浮现在脸上,“想听是吧,成,那我就告诉你。”
齐海说着就站了起来,还撸起袖子,脚下踱着碎步酝酿着,最终说了他这辈子都不想跟自己儿子承认的一个事实。
“你老子是个深柜,也喜欢男人,他给你找了个后妈却是个男人,”齐海几乎是一气呵成,“这个回答你满意了吗?祖宗。”
齐海最在乎脸面,而齐麟逼他向自己坦白,就是狠狠在打他的脸,戳他的心窝子。
可父子对抗,终归不是仇人的博弈,齐海选择认输。
齐麟心狠狠抽了一下,他没有继续拱火,而是问:“您爱李叔吗?”
“爱,”齐海气呼呼的咬牙道,“爱死了!”
齐麟闻此便退去了刚才的愁容和神伤,他提高了些音量,确保厨房门口的男人也能听得见,他说:
“我同意,从今天起,叔儿也是我爸。”
齐海猝不及防,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嘴上却一点不认怂。
“你当我稀罕,你同不同意这事都没商量,我是你老子,我跟谁在一起,你都得给老子认。”
齐麟木然,真不知道李维宁到底看上齐海什么了?这人就是个嘴硬又嘴贱的独裁者。
其实齐海说完就有些后悔了,于是心虚的又补了一句:“但是你能这么说,我、我很…欣慰。”
齐麟心里翻了个大大的白眼,鬼扯的欣慰,明明就是感动的要死,就会死鸭子嘴硬。
“齐麟,”李维宁是时的喊了一声,“过来端菜。”
齐麟的声音也敞亮了起来:“好,来了。”
人一走,齐海按着鼓动如雷的胸口,长舒了一口气,“兔崽子,吓死人了。”
不管怎么说,一家三口难得又聚在了一起。
“你和陈既庸一切都好?”李维宁说着又给齐海碗里夹个鸡翅膀。
齐海夹起鸡翅就啃了一口,就怕自己话多,又说不该说的了。
“嗯,挺好的。”
“那就好,”李维宁又给齐麟碗里放了个鸡腿,“吃吧。”
齐海哼了一声,“我也要吃鸡腿儿。”
“你胆固醇偏高,一个翅膀,不能再多了。”李维宁语气温和却丝毫不给人拒绝的空间,“你跟儿子抢什么?”
“一只鸡两个腿,”齐麟突然又突兀的问:“介意我再叫个人来吃吗?”
齐海一口米饭喷了半数出来,跟着就是一阵猛咳。
李维宁无奈的摇了摇头,赶紧给人递了纸巾,“慢点。”
“算了,还是以后再说吧。”齐麟继续低头吃饭,想来是自己操之过急了。
然而齐海却突然松口了,“把人叫过来吧。”
齐海和李维宁都倍感意外的看向齐海。
一家之主嘴角挂着大米粒儿,清了清嗓子道:“怎么?还得让我再说一遍?”
齐海深知事到如今,他能做的太少了,家里两个祖宗早就达成统一战线了,他孤家寡人根本无力对抗。
加之齐麟今天承认了李维宁,那他总得拿出点气度来,不是吗?
陈既庸没想到,齐海居然同意他进门。
他从夏雨那接到齐莽,之后去刘冬冬那转了一圈,冯启明出国还没回来,说等他回来再约。
这会儿他正开车回奥朗,齐麟就来了电话,说让他去接一下,陈既庸没多想,直接改道齐家。
二十分钟不到,他人就到了。
这个庄园式的大别墅,是他第二次来,上次他只能把车停在大门口,而这一次,有专人给他带路,把他带到了最深处。
他杵在齐家门口愣是没敢动,而是选择给齐麟发了消息。
陈老师:宝贝,他们把我领到你家门口了,我害怕。
齐齐:进来。
陈老师:你确定你爸不会拿扫把把我扫地出门?
齐齐:我家没那玩意。
陈老师:可以不进吗?
齐齐:进来!
陈既庸束手束脚的,紧张够呛,犹豫了半天才要按门铃,然后门就开了。
“怎么这么慢?”齐麟见人迟迟不进就出来接了。
陈既庸压着嗓子小声道:“什么情况?”
“先进来再说。”
陈既庸真是一点准备都没有,主要是心里上没准备,小朋友注意真是越来越正了,欠管教。
陈既庸心内相当复杂,但还是要保持成熟中年男人的体面。
“又见面了,陈先生。”李维宁率先开了口。
陈既庸心里打着鼓说:“我这还没来得及准备什么,就这么过来了。”
“陈先生见外了,”李维宁嘴角带笑,“是我们唐突了,这个时间让您过来。”
齐海始终不吭声,心里腹诽着:老子可没想同意,还不是你们娘俩逼的。
为了等人来,桌上的菜几乎没怎么动,这会儿已经有点凉了,李维宁又说:“齐麟,跟我去把菜热一下。”
“好,”齐麟看向陈既庸,让人别紧张,“你们聊。”
陈既庸瞳孔睁大,硬着头皮挤了笑容出来,“好。”
齐海那头也好不到哪去,恨不能跟着去厨房热菜好了。
客厅眼下就剩两人一狗,齐莽来回在两人之间转悠,找存在感。
“这狗,胖了不少。”齐海心一横,没话找话来这么一句。
“啊,”陈既庸只能应声,“齐麟总偷着喂它罐头。”
“啊,”齐海眼珠子乱转,“罐头好啊,全是肉。”
陈既庸嘴角的笑容已经僵了,“对,胖点好。”
俩人都是在各自圈子的体面人,也算是同龄人,齐海比陈既庸年长几岁,但是俩人碰在一起聊个天的水准,却是连幼稚园大班都不如。
“那啥,你放松点,”齐海终于受不了,他快疯了,“咱们都正常点。”
“好,正常点,”陈既庸不尴不尬的也笑了出来,“您比我长几岁,那我叫您齐哥吧。”
齐海卡了半秒,这是怎么论的呢?
“行,老弟。”
陈既庸僵化,笑了笑却没再好意思叫哥。
等齐麟他们出来的时候,却发现客厅没人了,齐麟四处看了看,人呢?
不是外头打起来了吧?
齐麟抬脚就往门口走,但是被李维宁叫住了,“他们在楼上。”
“去楼上干嘛?”
“你爸那些个宝贝要搬到博物馆,打包前想让你家那位给拍些照片。”
齐麟皱眉,第一反应是大材小用,第二反应是凭什么?
他的人,轮得到别人使唤吗?哪怕那人是他爸,再说,给钱吗?
“我上去看看。”
齐麟转身就往二楼走,刚上了两个台阶,长廊尽头传来了一阵说笑,声音由远及近。
“干嘛都堵这?”齐海问。
“齐麟怕你欺负人呗。”李维宁故意说的暧昧一些。
齐麟和陈既庸对视一眼,都有点难为情的意思。
齐海却说:“欺负个球啊,走吧老弟,咱们下去喝点?”
陈既庸点头:“乐意奉陪。”
“维宁你去开瓶酒,”齐海特意嘱咐了句:“要白的。”
“好,”李维宁笑着又说:“我刚又炒了个菜,给你们下酒。”
一旁的齐麟只能让路,这什么情况?陈既庸投给齐麟一个安抚的目光,表示一切都在掌控。
看着三人走向饭桌的背影,齐麟突然就不知道是要开心,还是要担心了?
他爸很少在家里招待人,从来不开白酒,这明显是要罐人的节奏啊。
果不其然,这顿饭以陈既庸的不省人事收尾。
齐海是海量,陈既庸根本不是他的对手,虽然看出来齐海有意罐他,但他欣然接受,并没有像常规酒局那样半推半就,能少喝点就少喝点,极是坦诚。
这酒,一杯不少,他都喝。
齐海是典型的性情中人,从酒桌上起的家,他习惯了拿酒看人。
不论是虚与委蛇、真情假意,还是阿谀奉承有所图谋,一上酒桌,原形毕露。
酒精不会骗人,喝了酒,人就没了大半的伪装,什么牛鬼蛇神在他的酒瓶子下,都得现原形。
陈既庸十几二十年没这么喝过了,还是白酒,但他并不担心自己酒后失言冒犯了“老丈人”。
因为,齐麟绝不可能看着他被人欺负,他只管喝,会有人给他善后。
酒过一巡,齐海只是微醺,陈既庸眼球已经红的不像话了。
齐海问:“老弟,你眼睛怎么是蓝色的啊?是有啥病吗?”
“爸,他是混血。”齐麟就烦齐海叫人老弟,嘴还那么贱。
陈既庸暗处握住了齐麟的手,笑了笑说:“我父亲美国人。”
“那你混的不明显啊,不是这眼睛,根本看不出老弟你是双血统。”
李维宁斜了齐海一眼,别说了,一点不好笑。
齐海赶忙乐呵呵的又补了一句,“但挺帅。”
如果说一巡是轻飘飘、撒撒水,那么二巡就是有惊无险。
而这三巡酒,却是暗潮激荡,危机四伏,然而此时,陈既庸脑子已经木了。
考验心性与意志力的时刻到了。
齐麟见人都快喝蒙了,于是去厨房煮醒酒汤,李维宁也去了。
齐海像是看准了时机,突然问陈既庸:“你能爱齐麟多久?”
那一瞬间,齐海脸色是极阴沉的,就好像之前笑脸相迎的样子,都是假象。
虽然靠山不在,可陈既庸也是没在怕的。
他将杯子里刚满上的酒,一饮而尽,酒杯啪地一声落回饭桌,齐海和齐莽均是一激灵。
陈既庸忍着嗓子干涩,气管的灼痛,一字一句,铿锵有力的说了四个字——往后、余生。
说完,陈既庸一头扎在了桌子上,带着那份决绝和坚定,带着对齐麟的忠贞爱意,坠入了无人之境。
此后人声、狗吠,整个世界,都与他无关。
后来陈既庸怎么回的家,他一点记忆都没有了,但是他这一晚睡的格外安稳与满足。
他于黑安与虚无中飘荡,却不担心自己会迷路,他能清晰的感受到,有一片温暖正源源不断的环绕着他。
他更听见有人在唤他,那声音如悦耳的雨后风吟,温柔中透着舒心的冰凉。
那声音,在说爱他。
陈既庸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下午。
窗帘拉着,屋内昏昏沉沉,跟他人一样,陈既庸迷瞪着下了床,想找口水喝。
不得不说,这酒贵是有贵的好处的,比如他现在只是感到疲乏,头却不疼。
他步子懒散的出了卧室,就见齐麟正往客厅搬箱子。
“醒了?”齐麟放了箱子到地上,“门外还有几箱,你去搬。”
“?”搬什么?
“我爸叫人送了茅台过来。”
“?”为什么?
“他说你爱喝。”
“?”这是讽刺谁呢?是觉得他买不起茅台吗?
“他没别的意思,他还说,你要是介意,也可以把这十箱酒当聘礼,嫌少他托人再买。”
十箱……
“够了。”陈既庸狠狠搓了搓脸,抬脚去搬“聘礼”了。
至于为什么不是“嫁妆”,陈既庸没问,昨晚那几瓶酒余韵太盛,聘礼就聘礼吧。
时间转瞬,一晃陈既庸已经回来快一周了,扎西打电话说,明天的回组的机票已经买好了。
陈既庸叹着气挂了电话,他就要走了,离家综合症正狠狠折磨着他。
相反,齐麟就很淡定,陈既庸看得出,人是真淡定,跟上一次的表现相比,判若两人。
陈既庸本想跟人抓紧时间腻味一会儿,齐麟却说有事要出去一趟,让陈既庸自己收拾行李。
期间齐莽跳进行李箱,眼巴巴的看着他,还叫了两声,可爱暴击,陈既庸更加不想走了。
直到齐麟回来,行李箱还空着,陈既庸人在沙发上躺尸一般。
“要一起下去溜齐莽吗?”齐麟问。
陈既庸一听,心里终于见了点阳光,“好啊。”
入秋之后,天气凉的很快,奥朗不大,但是慢悠悠走一圈也得半个钟头。
夕阳染红了天边,秋风裹着凉意。
齐麟牵着齐莽在前,陈既庸慢了几步在后,他拿出手机,朝着一大一小拍了一张。
咔嚓一声,惊动了前面的人,跟着齐麟回眸的瞬间,就再度被定格了下来。
余晖下逆光而立的大男孩,不、是真正的男人,他陈既庸的男人,正身上披着霞光,无比耀眼。
陈既庸驻足晃神,如信徒仰望着神像金身一般凝望着齐麟。
那瞬间,他自视平庸的人生,锦上添花了。
齐麟看着傻愣着偷拍他的人,嘴角上扬的弧度被阴影挡住了,他朝陈既庸伸出了手。
“快过来。”
被点了穴一样的人,赶忙两步变一步,迎了上去。
他们双手紧握,面朝晚霞,踏着惬意步伐,单看背影,谁又能知道他们是年龄相差悬殊的恋人呢?
齐莽也蹦蹦哒哒,想要抱抱,但是没人再愿意抱一只体重超过十公斤的……小型犬了。
此时就在不远处,抱着比熊的女孩,正看着手机,嘴角笑意飞扬,想着刚才的偷拍应该没被人看到。
秋高气爽,首都机场。
陈既庸在候机室里发消息给齐麟。
陈老师:宝贝,我快登机了。
齐齐:嗯。
陈老师:宝贝,我想你了。
齐齐:嗯。
陈既庸以为齐麟会如之前一样来送他,结果人家说约了球,比他出门时间还早,改换刘冬冬过来送他。
他情绪不高,还说以后不想接这么耗时间的活儿了,刘冬冬自然看得出陈既庸闹什么妖,直接数落了他一路。
眼下催促登机的calling响起。
商务舱的登机要早一些,落座后,陈既庸看着远处机窗外排队起飞的飞机,又看了眼手机,咳,睡觉!
他这次是坐外侧,里面的座位还空着,估计是没人。
有那么一瞬间,陈既庸竟然想,如果同行的人不是自家的小朋友,那就永远空着吧。
陈既庸觉得自己真是魔怔了,自嘲的笑了笑,随即拿出眼罩,合了眼。
过道里来往的人断断续续,突然一个声音从头顶传来。
“麻烦让一下。”
沉沉的青年男音,让陈既庸的身体本能的一惊,他以为自己幻听了,连忙扯下眼罩。
抬眼看去的瞬间,捕获了棒球帽下一双深邃眼眸,还有嘴唇一侧不显眼的张扬笑意。
“陈老师,又见面了。”
是啊,昨晚还睡一张床的人,分开也不过三四个小时,竟然又见面了。
 成功加入书架
成功加入书架